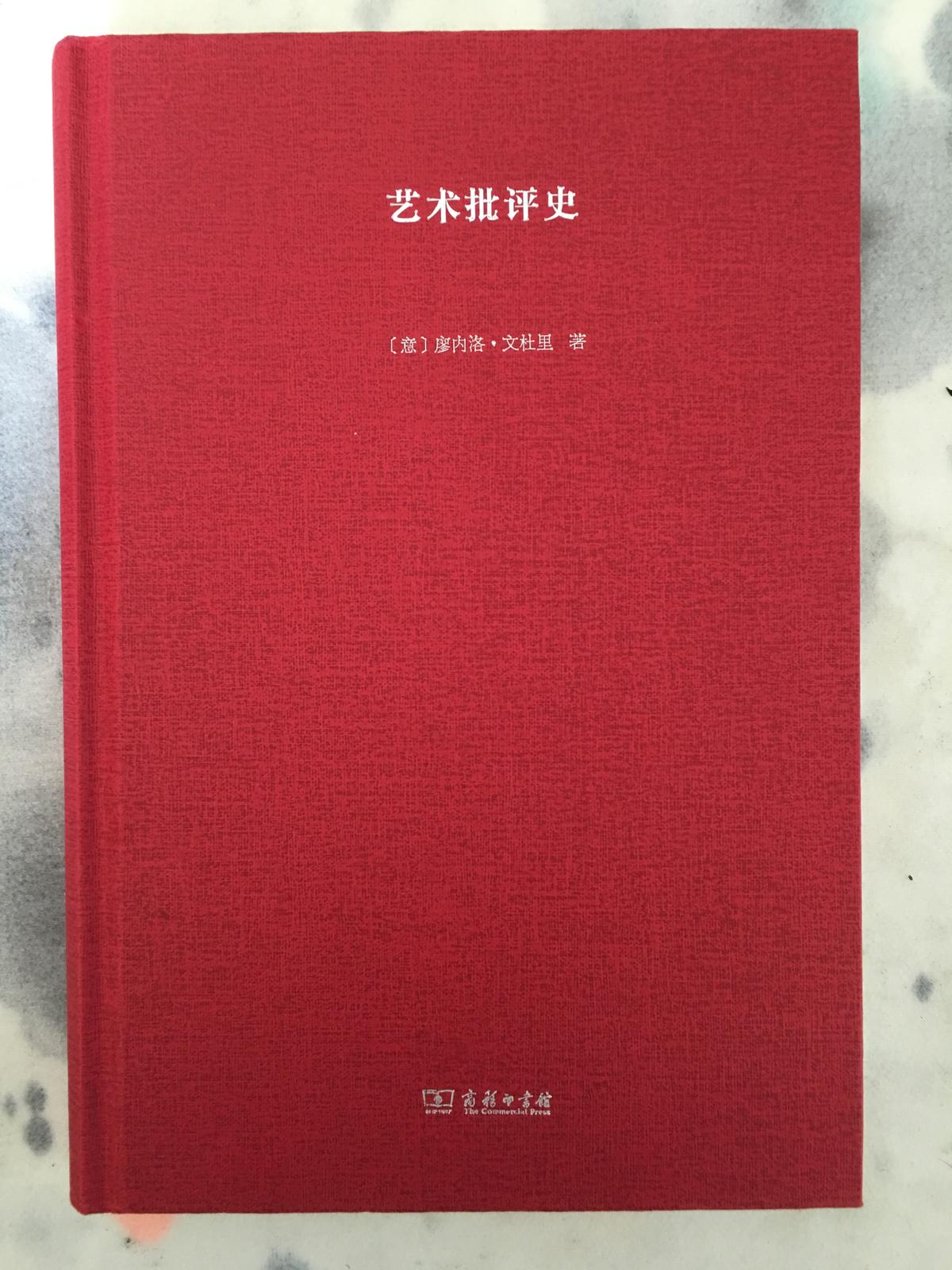裴满意|对意大利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的转述与阐释
艺术史不能沦为编年史,我们呼唤批判性的艺术史书写
文杜里《艺术批评史》这本书最早写于1936年,1948年重版时作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现代艺术》一章。该书也是英语世界第一部艺术批评史专著。目前国内比较好的翻译本有两个。一个是2005出版,迟柯翻译的《西方艺术批评史》,作者名字译为里奥奈罗·杜文里;另一个是2017年邵宏翻译的《艺术批评史》,作者名字翻译为廖内洛·文杜里。两则各有优劣,读者可自行选取。笔者以最新出版的邵宏翻译的《艺术批评史》为读本。
本书共有十四章,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其中的三章,即第一章、第十三与第十四章,此三章基本集中了作者的思想精髓,其他第二章到第十二章都是这三章中理论的申述与阐释。
文杜里在第一章中首先简要的介绍了艺术史研究的现状与艺术批评史的重要性,他认为艺术史不能沦为编年史,要深入到人类的心灵中去挖掘历史事实审美价值的阐释,而不是像实证主义时代那样在研究的过程中摒弃思想与思考。于是,完成修正艺术史研究的指导性标准以及反思艺术史、艺术批评与美学之间关系的契机正要来临。这一看法在今天已经是常识性的了,但是作者能在20世纪的30年代提出艺术史学上的这种缺陷,可见文杜里极具史学批评洞察力的。
艺术史与艺术批评存在一种双重困境,即历史与批评双重标准无法统一的尴尬。批评需要判断,但是判断又需要历史事实。如果所指的事实不视为用于判断,那事实就毫无价值;如果判断不依赖对历史事实的了解,那判断就全然错误。亦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直觉的概念都是空泛的,没有概念的直觉都是盲目的。但是这两者并不是不可协调,文杜里在书中例举了贝内代托·克罗齐曾以一种值得效仿的方式分析过此困境。对上述困境的解决方案便是:
艺术作品无疑具有自身的价值,但是这个自身不是简单的、抽象的,不是一个算数单位,相反,它是复杂、具体、活泼的,是一个有机组织、一个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整体。要理解艺术品,就是以部分去理解整体和以整体去理解部分。
——[意]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17页
在分析完了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的同一性之后,文杜里便开始探讨另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批评性的艺术史研究与美学的关系。他认为总体上美学是有益于艺术批评的,但是艺术批评不全然是美学的问题,光有美学或哲学是无法完全解决艺术批评的困境。此外文献学的著述、美学理论或趣味性行为都不能充分地体现出艺术批评。
那么如何才能体现出批评呢?文杜里认为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艺术判断”。他在书中举波德莱尔为例子,给予说明,因为:
波德莱尔的行为中心恰恰就在于判断;他是绝对意义上的批评家,因为他是以判断为中心的。
——[意]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23页
那么什么是“判断”呢?他认为考察判断,需要分析几个重要的因素:
1. 实际因素(由判断所针对的艺术作品来确定)
2. 理想因素(批评家的审美观念以及通常由他的哲学观念和道德需要来确定——总之,由批评家所追随和帮助形成的文化来确定)
3. 心里因素(它取决于批评家的个性)
在这个三个因素中,心里因素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批评家的个性在文杜里看来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憎爱往往左右了批评的总体发展,正如我们普遍习惯说的,批评比批评家更有价值。
但是在这里同样有一个陷阱或是理论逻辑的缺陷,也即是否意味着所有批评家的个性都具有批评的价值呢?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意味着任何人的胡说,都是批评。这样的批评角色,任何有个性的人都可以承担,也即瓦解了批评家的角色。故而文杜里在此提醒广大的批评家,所需要遵循的原则,那就是:
艺术判断的基本前提是具有艺术的普遍概念,同时在所判断的艺术家个性中辨认它出来。换句话说,艺术判断必须将艺术家的个性视作普遍艺术的表现,而具体的个性绝不能因任何有关艺术的抽象概念而遭到放弃。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需要具有判断的普遍原则;否则任何个人的无论什么偏好都会在历史面前得到解释,而不对真或假的判断,甚至好或坏的趣味作任何区别。如若是那样的话,艺术的历史本身不再是历史,而只不过是历史决定论,是纯粹的学识。
——[意]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25页
在艺术批评的过程中,涉及到很多方面,如美学、技术等,但文杜里通过几个不同章节的论述一一排除以上诸多方面,并在第十三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艺术的完美与物质性制作无关,却会存在于未完成之中。能够使他想到这些真理的,既不是他的美学,也不是他的技术,而只是他的直觉体验。
—— [意]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247页
由此可见文杜里重视艺术批评过程中的“直觉体验”。他在书中举例说明:
16世纪维纳斯批评和家们的感觉论[sensualism],也不足于使人想到他们未完成感认作是笔触、色调的明快,造型与色彩的综合,自发性,等等。指导他们的不是那些简单与粗陋的神秘观念,而是对提香和丁列托艺术的直觉体验。
——[意]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249页
在此也呼应了第一章里“判断”因素中的“理想因素”的批评观念的困惑,即:
批评家不仅通过先前的观念,而且首先是通过直觉地体验艺术作品,亦通过实际因素,来创造自己的观念。
—— [意]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24页
艺术的判断,其实也就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与直觉又相关,而观念其实又与批评家的美学或哲学观念有关。但是在第一章中杜文里早就论述过光有美学或哲学观念,是不能客观的解决艺术批评中的“判断”问题。故而在此又不免陷入理论的逻辑陷阱。亦正如文杜里在第十三章中的自我反问:
如果对艺术的判断在今天不能令人满意的话,这不是美学的过错,那错在艺术史学家的无知或误解吧?
——[意]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247页
为了突破这个逻辑陷阱,文杜里指出大家其实是误读了他所认为的“直觉体验”。他辨析到:
对艺术的直觉体验并不是艺术的直觉,因为这种直觉体验并不富有成界,它甚至不是批评,也因为它不包含人们做出判断时所具有的艺术观念。那它是什么呢?它是批评的感性阶段,是个体的领域,仍然太个人化而无法具有普遍性;一句话,它就是趣味。
—— [意]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257页
紧接着他又指出,批评家不仅仅要对现在、当下的艺术要有直觉的体验,对往日的艺术也同样需要。
在此文杜里举了一个反例给予说明。
他批评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著作,认为其审美的观念是保守的,是属于贝洛里到门斯的传统。而这一传统优势来源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理念,并进一步分析认为,温克尔曼是学究式的研究。他对艺术的直觉是愚钝的,并未受到他同时代的艺术影响,且缺乏对艺术个性以及艺术非理性的直觉感受。但是温克尔曼却具有超强的历史感,他对艺术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更敏锐,故而其写就了一部新型的演变史。但是这种演变史,在杜文里看来事实上是一部有关各种艺术方案和类型的历史,而不是有关艺术的,却假托了艺术史之名。
不幸的是温克尔曼对19世纪的美学和艺术史具有重要的影响,要摆脱并跳出温克尔曼对艺术史的错误理解,极其困难,故而杜文里认为他是艺术批评领域最大的障碍之一。
看来杜文里十分注重艺术史学家或批评家对同时代艺术的关注,亦正如格雷戈里·巴特科克为其著作《艺术批评史》所撰写的引言中所判断的一样:“任何批评家都无法脱离与自己时代艺术状况的联系。”
紧接着杜文里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以上观点,那就是批评黑格尔的美学理论。黑格尔不仅继承了部分温克尔曼的观点,诸如认为“希腊雕塑不可企及地完美”,并指出“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此外黑格尔把艺术分为三个阶段,即象征—古典—浪漫,若从此出发,必然会从这种理论体系中推出艺术到现在要死亡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直到今天艺术依然在蓬勃发展。故而杜文里认为,尽管黑格尔是一个伟大哲学家,但依然不免受到温克尔曼的影响,而导致其美学将艺术批评引向歧途。
于此相对,杜文里比较赞同托雷,因为他充分代表了现代艺术中泛神论的理想,强调艺术回归到源头,此源头不是历史的源头,而是心理的源头。并进一步认为弗罗芒坦的《往日的大师》是19世纪一部史学史出类拔萃的著作。因为他对正在发展中的艺术的生命的热切关注替代了以为清晰的审美观念的分析。他是在对同时代艺术具有深刻体验的基础上,来讨论并判断往日的艺术。例如他关注佛兰德斯和荷兰的艺术,发现它们与自己所处时代的法国当代艺术有关,而不是先入为主的做出以上判断。
在此人们不禁又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趣味”是否具有统一性,即过去的与未来的“趣味”是否具有可比性。
聪明的文杜里,给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他敏锐的分析出艺术是绝对的,而趣味是相对的。
这样就能避免各种随心所欲的偏爱,避免建立用于判断的各种模式,避免有关进步与衰落的概念——总之,避免所有艺术家个性的误解。对现时趣味的需要也不会妨碍批评家辨认不同的趣味。相反,批评家越是懂得现时的趣味,他就越是清楚它的局限,也就越是辨认得出超越那些局限的东西。
—— [意]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257页
那么如何获得这种“趣味”呢?
杜文里认为趣味中包括所有科学的、宗教的、道德的和实用的动机;艺术家在创作时怀有这些动机并赋予它们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其强调要获得趣味需对文化史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文化史不再与艺术作品相分离的。对文化史的研究,有利于艺术史的研究。正如其所认为的“趣味曾通过穿越心灵的所有领域而对艺术作品的直觉相分离;现在,它又返回到对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个性的直觉中去,却饱含着全部的人性”。但是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人性是不一样,就如同一种画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一样,既可能产生杰作,也可能出现平庸之作。是一种观看与感觉的方式的变化,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一种趣味的历史。趣味本身是历史,也是艺术。艺术史也应该研究、分析并描述这种趣味,其目的就在于发现由于天才的影响而使趣味成为艺术的时刻,而这一时刻就是艺术史研究,也即批判性判断的时刻。
可见,批评家是要有直觉意识到当代艺术的发展,从而在现实的基础上去判断过去与现实的关系,从而区分绝对与相对、永恒与短暂、超越历史的价值与受这种价值支配的现实。如此才能真正的区分艺术与趣味。因为在杜文里看来,一个人只有拥有自己文明所承认的最完善的趣味,才能理解昔日文明或遥远之地的趣味,且能觉察出无论是身边还是往日的绝对趣味与相对趣味。
以上是前面十三章的主要内容,最后一章是“结束语”,对前面的申述作总结。再次强调对当代艺术的体验能使我们理解往日艺术。趣味是分析艺术作品的契机,更是连接天才的创造与历史发展的桥梁。
一个批评家应该有培养批判性的头脑。正如其言:
面对当代艺术作品的人不要求助于已确立的、明确的批判标准和权威传统。他同样必须重建创造性的想象力的来源,发现智性的不同组合和那些意在充作艺术的诡计,在选择与拒绝中培养批判性的头脑。
—— [意]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262页
由此可见文杜里注重在直觉体验的过程中,对历史与未来做新的判断,这种判断则考验着一个艺术批评家的能力,他需要完备、睿智的慧悟来抓取或摒弃艺术当中毫无内涵的东西,而整全的把艺术作品的灵魂与精华诠释出来。
这也是其一再认为的,即批判性的艺术史研究与传统的艺术的最大区别,那就是其自身的批评功能,而批评的中心关注点是艺术家的个性。从而得出对艺术的历史研究取决于对艺术的批评这一批判性艺术研究的原则性结论。
以上便是这边书的主要内容,虽已距今80来年了,但是在今天看来依然处处闪现着智慧的光芒。他敏锐的指出批评性的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性,并给出了自己的批评路径,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这种尝试是极具思想价值的。总记得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有一句话,其言:“人是一个世界,也有自身的造物,人自身的造物是人的思想,思想生来了不起。”
笔者认为文杜里的几个观点依然有益于当下的艺术批评研究。
首先便是建立在对当下艺术的直觉体验,来打通历史与未来的桥梁。这个观点在学理上有高屋建瓴式的作用。是一种寻找艺术直觉的实践性活动,有利于艺术批评家找到批评的现实路径和渠道,而不至于让批评陷入毫无普遍性概念的空洞无边际鉴赏与情感泛滥。
笔者认为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作品、艺术家等诸多因素构成的艺术世界带有批评性的体验、转述、再阐释的思想活动。但是在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角度的转换,都考验着批评者的艺术直觉与批判性思维。这个过程不是批评家简单的一个再参与环节,不是对作品等因素的再重读,也不是简单的艺术欣赏中的“共鸣”,而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是多方面的,有语言的,有叙事方法上的,更有思想上的。
批评本身就是思想的创造。它与艺术创作一样具有伟大的原初性与探索性。
“转述”,是人间一件极其困难、荒谬,并可能带来无穷祸患的事情。能客观的把握“转述”的人,是一个伟大灵魂。特别是转述有思想的灵魂的话语,这考验一个人敏锐的判断能力。要转述,则必然涉及到语言的择取与使用。
在笔者看来,人类的任何一部艺术史,不管是作为历史的艺术,还是艺术的历史,其实都是一部语言的历史。
康德认为判断力,是一种先天立法的能力。我则认为对语言的使用才是一种先天的立法能力。因为人是否有不一样的判断力,也依赖于语言使用的独特性与专一性。语言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有词语,有符合,有图像,更有肢体上的语言,乃至无声的声音。在此意义上,不管是海因里希·沃尔夫林所指的“最普遍的再现形式”,还是贡布里希、夏皮罗等所乐道的“风格”,于贝尔·达弥施、诺曼·布赖森、欧文·潘诺夫斯基等所谓的“图像志与符号学”,乃至20世纪后半期的观念艺术史,其实都是一种语言的“转述”,是语言上的观念史。
正如戴维·萨默斯所说:“我们应该开始讨论艺术史的描述性语言。将图像转换为词语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切事物都要遵循的方式。”
要做到文杜里所阐述的真正的直觉体验的确很难,因为理解、参悟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困境。
“再阐释”,除了可借鉴诸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的思想之外,美国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的思想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参考。阐释艺术有时候就像用特定的方式试图把某些事物放在某种可以理解的、有意义的系统之中一样。阐释的根本使命不是回答最深刻的问题,而是以一种独到的方式得以接近“他者”。
艺术在进行,在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在进步、在发展,此时的“他者”也类似。批评家需要敏锐的洞察到他者的变化,因为重复言说自己所领会到的他者是没有意义的。从这个方面来讲理查德·沃尔海姆的质疑性解释学同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批评的时代,其实是一个对语言再次定义与检视的时代。没有这个共识,谁都将不知道谁在说什么,因为你使用的语言并不能表达我所理解的意思。世界上不同的语言,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沟通的,但是语言概念的入侵与混乱,是这个时代文化艺术理解的最大障碍。
一件作品对另一件作品来说,完全是一个谜。即使同一个艺术家的不同作品间的随机性,以及其所展现的个体心性,也是有着巨大的差异性,能否扑捉这里面精微的变化,是衡量一个艺术批评家感受力的标准之一。
其次便是文杜里一再强调的“个性”。他这里所谓的个性,乃是艺术家的个性,此个性是个性本身的法则。他认为:
“这种个性不同于一般老百姓的个性,因为艺术家的各性包含那么一个时刻,此时人的创造性想象力在造型与色彩中成为事实。知识的、道德的、宗教的以及所有其他的人类活动,都构成了围绕这一中心的历史,并帮助解释艺术家个性的本质,但只有取决于这一中心才有意义。
—— [意]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264页
但是笔者对文杜里所赞赏的“趣味”持批判的观点。趣味[taste]一词在西方造型艺术中其实是一个熟悉的概念。亦正如文杜里自己所考证的,早在1681年巴尔迪努奇便使用了“趣味”一词的双重含义。也即辨出最佳的能力和每个艺术家工作的方式。
文杜里把趣味的性质纳入到相对性的范畴下来讨论,这是其智慧的体现,因为如此能跳出理论推理的逻辑陷阱,但是也恰恰是这一点,却无法跳出时空人性变化的绝对性。趣味是相对的,对当下的趣味判断,并无法全然沟通过去的趣味。因为笔者刚才已经论述过,任何一个艺术家或艺术现象,哪怕是一个时代同一个艺术的不同作品都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人的趣味其实也都在随时变化,这种变化是断裂的、复杂的、碎片化的,甚至是随机的,不具有规律性和完整性。故而用“趣味”来达到识别审美与历史判断是徒劳的。因为不仅仅趣味不同,且言说不同的趣味所使用的语言也极具模糊性和混乱性,趣味也不具有穿越心灵的所有领域,其所认为的趣味“包含着全部的人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趣味的相对性,无法预设趣味的“例外状态”的各种可能性,它不具备概念与学理上的融超空间。这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堪称完备的理论都可能遭遇的悖论。人类也正是在这个不断争议与博弈中获得成长的力量,从而不断向理论的高峰迈进。
草撰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7-11-14夜
裴满意:独立文化学者、诗人、自由艺术家、艺术批评与策展人
江右古临川人氏,现生活于上海,幼秉庭训,接脉家学,吟诗属文,为艺求道。字非一,号苦口师、临川南斗,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治学主张以“心”为道体,古今中外为相用,理论与创作兼容,跨文化、跨学科、跨领域,盘活打通,文明互鉴,道艺互推。
研究领域涉及儒释道文化;中西方艺术哲学、文艺思想;当代艺术;现代书法与书写艺术;书画鉴定;中医文化;认知科学等,各类文章已过两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