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卫生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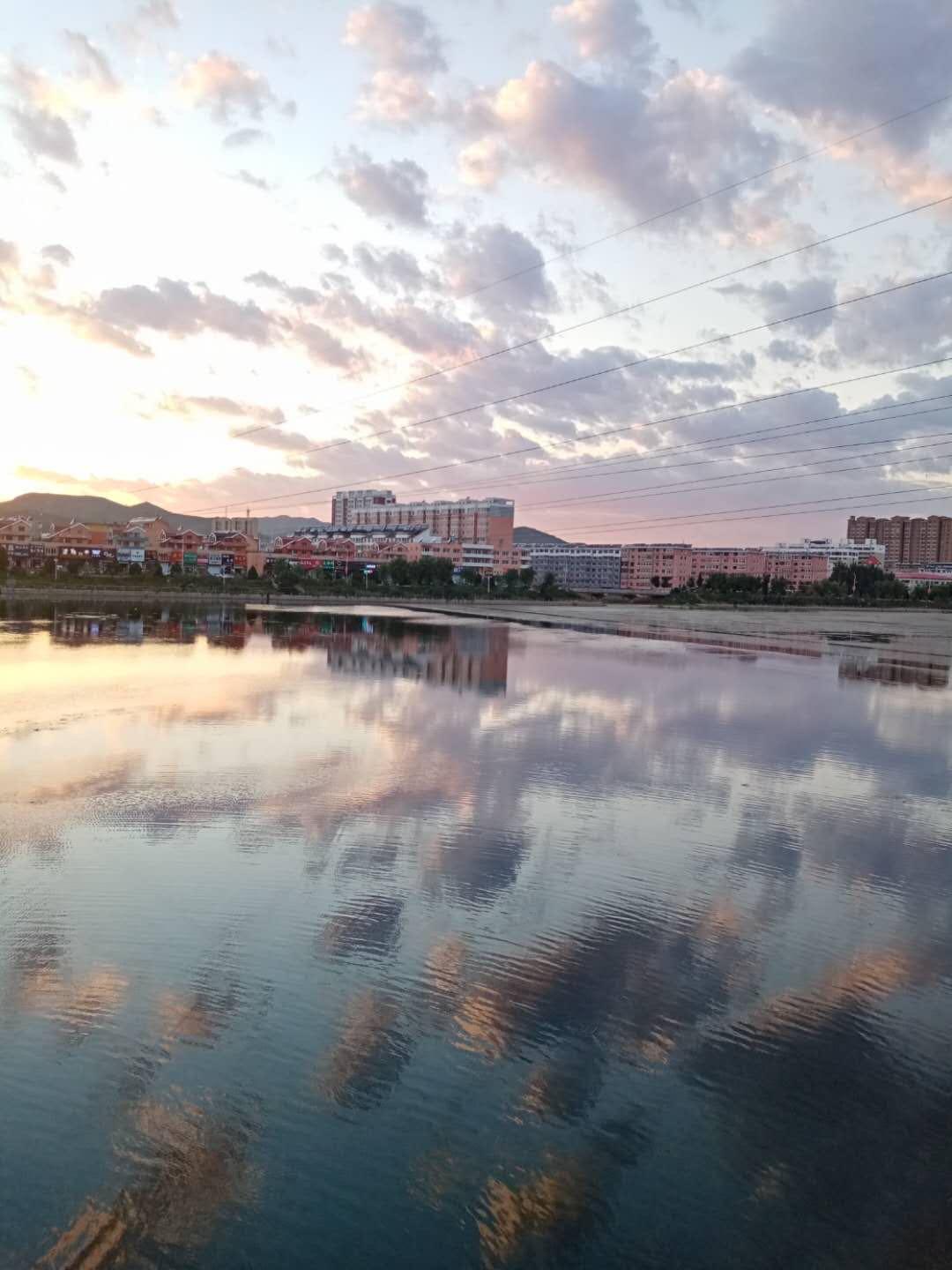
一一闲谈卫生间
心里不是个滋味,嗅觉上也是,因为要讲的是厕所,家乡叫茅坑,或臭所,北京老辈人叫茅房,现代文明叫法普遍称卫生间。村小学上学时,厕所在蓝球场旁一个斜坡下,夏天污水横流,味大,就是那种挖个坑,盖个房,门敞开着或根本没门,叫入口吧,坑位可能照顾老师,虽然用厕的大多是孩子,很宽,你能想像小孩子孱弱的小腿,岔开蹲在那里有多艰难。冬天里,污水冻成冰,味道小了,也得小心翼翼,不小心就会滑倒。记得那是冬季,我蹲在厕所,小学么,蹲下蜷缩了身子,显得人就是那么一小堆儿。村子里每家都有这样的厕所,村民在外做事的或路过,就近也共用学校的厕所。这时,一个村民从亮光的入口急急走进,直奔我而来 ,麻利的对准我占的坑位,我马上叫起来,他才掉转方向,真的好险。这人平时在操场边经常看到,是个俗称玻璃眼的,本来视力不好,又遇上使用这么个光线很暗的厕所。在北京,郊区和市中心都住过。那时的崇文门老住宅片区,就是一大片破烂四合院的,纵横着胡同,也是这种,大家共用的,北京人叫茅坑。电影里演的那样,每天早上起床后,污头垢面的去茅坑倒马桶。上个厕所,也要走出很远。厕所的坑位一溜排开,早上坑位还是紧张的,有的在厕外憋着呲牙咧嘴的转悠,里面蹲着的,有的看一块撕了的报纸,厕后用做厕纸。有的用双手把口鼻捂着,随着用力的节奏,脸不时的通红,太阳穴的血管凸起。有人厕毕,外面的人急不颠的冲进去,见了熟人,故作镇定,脱口一句吃了么。中国民间不知什么时候,用的你好这句问候语,应该是有了白领概念,在干净的办公室,才流行开来吧。在厕所,肯定没人见熟人蹲着,问候你好,好什么呀,拉个便谈不上好不好,正常生理需求。在郊区,也是这种茅房,那时也是一个院儿住了好几户外地人,房东在正房,坐南朝北的。去趟厕所也要走好远,快到村头了。经常在厕所遇上对门的男主,我叫他大哥,开小卖店的。他习惯是,蹲在那儿,总是用洁白的纸巾捂着口鼻。我进来,叫声大哥,他点头,脸上表情被捂着,我相隔而蹲,有时前伸头和他聊上几句,他回时,罩在嘴部的纸巾就扑扇几下。说说题外话,一天早晨去茅房,一出门,发现邻门的兄弟俩卖的小龙蚱,没盖住爬了出来,像是列队跟我抢着去茅房,一直冲出大门外。等我回来,院里也没人起来,真是无屎无尿不起早,我就捡了龙虾,有的夹住手指生疼。没吃过这玩意,不过,我有一个主张,就是没吃过又不会做,统统的水煮,至少杀菌不闹肚子,这在后来的南方生活验证了,叫白灼,还原味呢。去一趟茅房,吃一顿小龙虾,还是划算了。说一次尴尬的,在北京通州客运站,送完大哥,返回时去公共厕所,大家知道那时的全国各地,脏乱差的厕所都在各个火车站,客运站,人流聚集的地方。我来也匆匆的钻进门上挂布帘的厕所,没留意有没有男士站位设施,用了蹲位小便,这时邻位站起,匆忙推开小隔门冲出去,叫嚷着,管理厕所的冲进来,是个女的,你干嘛呀,怎么进女厕所呀。我已经厕毕,憋出句话,那哈,进错了。对方瞪着我。我说你看我像坏人么。那女的笑了,我看你不像好人。趁着这当儿,我去也匆匆了。还有,那时某种缘由,在北京房山区的十渡风景区,住了一些时日。房东新建了房做民宿,也无特色,与当地住宅无别,原来的老宅一个院我租了下来,一个人住下,经常去找房东聊天儿。一天傍晚,一队学生模样的女孩子,找到这个院,说话唧里呱啦的,房东也没怎么理,说听不懂说什么,可能是南方人。我也听不懂,但知道说的是日语。三五个去了茅房,又惊叫着冲出来,然后,这些小麻雀就全飞走了,那一定是这乡下厕所吓到她们了。还说老家,现如今的老家,一个北方的贫困县,县城里商业经济也不发达,公共场所,如公园里的,也还是那种老式茅坑,就连学校也是,以上说了,坑位宽度肯定要就大不就小,这下,小孩子们就得,上个茅坑,战战兢兢。 现如今,国家各方面好了起来,厕所问题那是相当大改善了。标志之一是,各城市的火车站客运站,卫生间都很漂亮,有专人打扫。就是我暂住的深圳市,一个社区临山的小公园,企业老板投资建设的,公益性质,卫生间建设堪比宾馆,也有专人打扫,也放置了厕纸。在想,如果吃饭在这样的卫生间解决,也不会感到不卫生。最后,希望我们都能用上好的卫生间,毕竟,这也是一种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