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巷——高名潞、費大為、栗憲庭藝術觀
三家巷
——高名潞、費大為、栗憲庭藝術觀

“意派”不是一個風格概念,它不是風格表現主義的,因為後者太注重“情緒”的直白表達和畫面效果。相反,“意派”是藝術家冥想的記錄和再現,它延續了東方美學的自然觀和冥想美學。
“意派”是有關關係的敘事。這個敘事不排除無意識和模糊性,也不排斥理性思考,也不排斥“形”,但是,“意”拒絕走向這裡的任何絕對和極端。……藝術家對“意”的追求不是對形式的、表現題材的或者單純自我感覺的追求,而是對整體狀態中那個精髓的追求。……捕捉到這個精髓,就不存在藝術是否再現了現實的問題了,因為自己、世界萬物都是一體的,是不可分割的現實世界的整體。
西方抽象藝術、觀念藝術和寫實藝術都強調某種極端分離性。似乎抽象就是完全“形而上”(概括形的原理)的,觀念藝術是“形而外”(排斥以形為先)的,寫實則是“形而下”(模仿形)的藝術。而“意派”試圖擺脫這個形而上、形而外和形而下分離的美學。……因為,無論是現代主義還是後現代主義,它們在詞語與形象間的矛盾、符號與象徵間的矛盾和局限性都可以在意派的理、識、形整一性理論中得到解決。因為理、識、形的空間關係制約了任何一方,不使其脫離整一關係,三者在變化和運動中保持“似似而非”的外觀,也就是“理非理”、 “識非識”和“形非形”的特點。但是,這些“似似而非”的,或者說是非飽和的理、識、形的結合恰恰達到了一種契合——“意”。
“意派”應該是一種自足的理論,我希望它即可以作為一種批評理論去闡釋藝術作品和藝術現象,另一方面也是對一種藝術美學的描述和概括。
——高名潞《意派論——一個顛覆再現的理論》
 《伊索寓言》(胡志颖作品)
《伊索寓言》(胡志颖作品)
世界在變,民族也在變;只要我們看看現在全球的文化交流規模之大,影響之深刻,以及在西方各國的外國藝術家人數之多,國籍之繁雜,在創作上呈現的千姿百態,也許我們就不能匆忙得出“藝術離開其文化母土就必然枯竭”的結論了。不過,“枯竭”也是一個普遍的、正常的現象,國內和國外不都有大批藝術家正在“枯竭”嗎?要保持旺盛的創作力主要並不取決於你在國內還是國外,儘管這兩地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是非常不同的,但是藝術創作的根本問題是超越國界的,好的藝術家不管在哪裡都可以利用環境的特殊性使其最大限度地為自己的創作服務,文化環境的變動本身就可以成為靈感的源泉。
我們還可以把這個問題換一個方式來看:如果我們從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的角度去確定“家”和“祖國”的概念,那麼出走在特定的條件下便可以解讀為一種“回家” 的方式。一個封閉的文化有時會象一堵牆一樣把人的身體和精神分割開來。在這種文化氛圍中,人的精神存在往往處在流離失所的狀態下:身體的“在家”往往成為精神“無家可歸”的原因。因此,另一種意義上的“流亡文化”恰恰可以在一個文化內部發生。
“流亡文化”令人想起的另一層含義是:這些藝術家被迫脫離了他的創作方法所決定了的固有創作源泉和固有的接受者,因此變成了一種被懸置起來“晾乾”的藝術家。在有很強的現實主義文藝傳統的蘇聯,政府常常把持不同政見的文學家驅逐出境,以此作為一種殺手鐧,曾使不少作家聞風喪膽。但是,只要我們看看那群星燦爛的蘇聯、東歐的“流亡作家”在西方所取得的成就,我們就不難明白,並非一切創作都必須被綁在一個固定的地點和固定的接受者身上的。“流亡文化”如果真有一部分“枯竭”掉的話,那僅僅是由於他們的思想方式的封閉和凝固所造成的,這部分人即使不流亡,恐怕也同樣會落入“枯竭”的境地。
渥霍和波于斯從來沒有追求過什麼“德國藝術”、“美國藝術”的特性。與他們的藝術相比,那些追求“民族化”的潮流難道不是一種很可憐的地方主義情緒嗎?最近十年來,西方藝術中的民族情緒又以十分曖昧不清的方式略有抬頭,那也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和東方國家所提倡的“民族化”完全不是一回事。後者所提倡的“民族化”除了用來做成文化鐵幕以外,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文化意義。
——費大為《關於“流亡文化”與“民族身份”》
 《凱努比諾的詠歎調》(胡志颖作品)
《凱努比諾的詠歎調》(胡志颖作品)
對西方諸漢學家的觀點,我當然不贊同,他們無非是獵奇心理。但藝術不是智力遊戲,更不是雜技。一個藝術離開了他的文化母土,則必然會枯竭。向來的“流亡文藝”都只是在歐洲大文化背景中進行的,即是同一大背景,渥霍與波依斯就分別打著各自的文化烙印。當然這得承認國際新價值標準為前提。民族化不是官方說的那種,但不是沒有這個東西。不能以現代主義的所謂原則性的方式,去從事當代西方的後現代主義的樣式。在當今世界上,已談不上什麼“前衛”了,無論你幹什麼,都會似曾相識的。
我們說他是藝術家,而不強調他是一個畫家,一個雕塑家,一個攝影家,是強調看一件藝術作品,不把畫種“行業標準”作為評判藝術的標準。如一張油畫,他畫得像不像傳統油畫,有沒有傳統油畫味道,不再重要,造型準確與否,也不再重要。要看的是,這張作品是不是提供給觀眾一種與當代人生存有關的新感覺。所以一些當代藝術家往往不局限某一種媒質,某一種畫種,或者今天畫油畫,明天可能作行為。當然,因人而異,一個藝術家可能只善於使用一種媒材,但他的作品依然不是傳統畫種意義的攝影或者油畫。
中國藝術原來是面臨意識形態的壓制,90年代後期以後,就變成商業和意識形態的雙重壓力,就是不在宋莊在別處也一樣。文化創意產業在某種意義上等於給官商拉到一個“道場”。如果藝術作品存在免稅制度,不法官商多半會利用這種制度作為洗錢的途徑,因為目前還沒有監督商業機制的機構,缺乏監管。事實上藝術的成長必須跟整個社會體制相適應,根本問題還在於體制、機制。
過去跟現在一樣,理想主義每個年代都有,現在也不是沒有理想主義。但總體來說那時候因為沒有商業化,好像理想主義很突出而已,我經歷過過去的時代,那時候一樣地封展覽,抓人比現在還厲害。包括90年代初,因為做行為藝術被抓進去勞改,勞動完了遣送回去,其實比現在嚴重,因為現在網路很發達不容易掩藏。過去的整個世界所發生的醜陋的事情一樣的多,只是沒有揭露出來那麼多,本質上沒有變化。沒有盛世,哪有盛世。
——栗憲庭《“前衛藝術”、“理想主義”、“意識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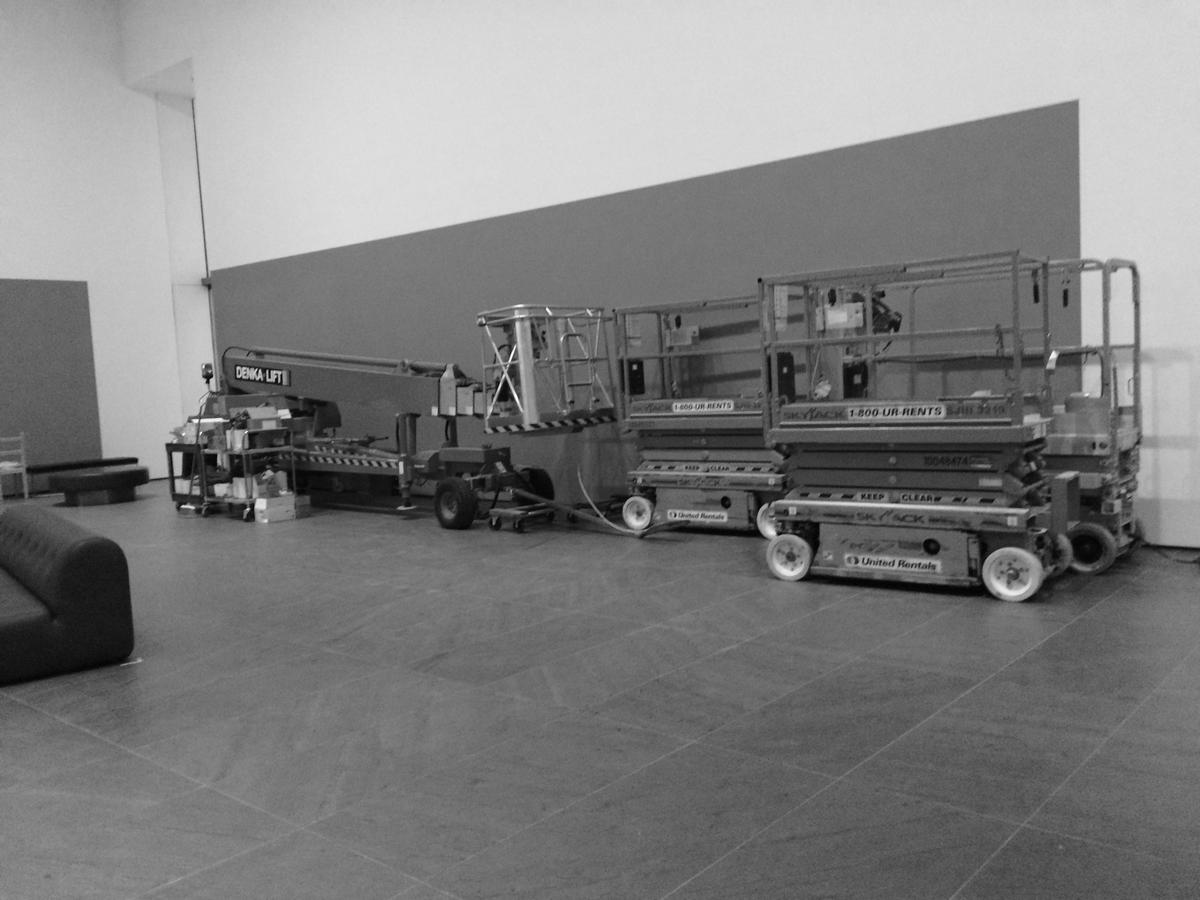 《安徒生童話》(胡志颖作品)
《安徒生童話》(胡志颖作品)
